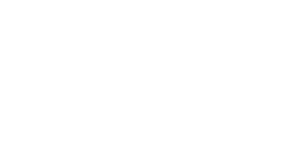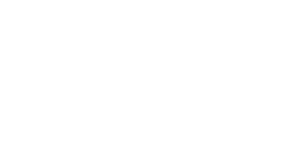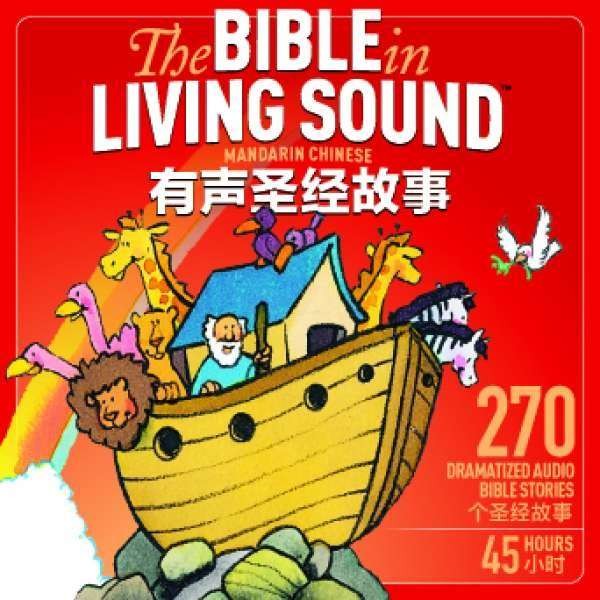定义人的身份01:了解人的身份_罗伯特 ‧ 戈弗雷博士
- 260
- 0
- 0
- 3
- 0
- 0
当今很多人声称,暴力并不是真的从人的内心产生的,而是外在的社会条件造成的。有人说,如果我们能把社会环境变好,那么人本性的良善就会展现出来。还有很多人说,暴力是人类进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身为动物而生存与争斗的必要条件。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圣经,也无助于理解我们在这世上观察到的暴力。
מילים
了解人的身份
编者注:这是《桌边谈》杂志:定义人的身份系列的第一章。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残酷和暴力的世界里。无论我们在电视上看地方或国际新闻,我们都会听到无数恐吓、不公、偷窃、殴打、谋杀和战争的案例。在某些地方,暴力似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另一些地方,暴力似乎在看似和平的地方突然爆发。我们该如何解释这样的暴力?
当今很多人声称,暴力并不是真的从人的内心产生的,而是外在的社会条件造成的。有人说,如果我们能把社会环境变好,那么人本性的良善就会展现出来。还有很多人说,暴力是人类进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身为动物而生存与争斗的必要条件。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圣经,也无助于理解我们在这世上观察到的暴力。
基督徒知道人类起初被造时是善良的,但却落入罪中,反抗上帝,也彼此疏远。如果没有上帝的救赎和更新生命的恩典,那么堕落的人心里就只有暴力而已。大卫在写到上帝对恶人的态度时,很好地表达了这个真理:“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诗 5:5-6)。”
在这段经文中,大卫强调了恶人的三个主要特征。首先,他们自夸和骄傲。他们认为自己很有价值、也很重要,远远超过事实;他们也不承认上帝比他们崇高。第二,他们充满了谎言和欺骗。他们按着自己编造的谎言过生活,而不是按着上帝的真理。第三,他们嗜血又崇尚暴力。在他们的骄傲和自欺中,他们愿意用残忍的手段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而不是追求爱与和平。
在《创世记》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这种恶行被实行了出来。该隐因为自私而谋杀了他的兄弟亚伯(4:8)。该隐的曾曾孙拉麦也表现出了这种自私。“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23节)。”
我们在该隐和拉麦身上看到的这种自私与优越感,也可以在历史上的许多方面看到。请想想看下面这段关于态度的批评;文中所批评的态度是大英帝国的基础:
大英帝国在多元民主社会的意义上并非自由开明的。这个帝国公然摒弃人类平等的思想,从英国人口中挑选出极少数的精英,并将权力和责任交在他们手上。大英帝国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我的论点是,就行政管理本身而言,虽然大量的种族傲慢显然存在于行政阶级整体当中,但阶级和等级的观念也是同等被看重的,甚至可能还比种族更被看重(Kawasi Kwarteng,《帝国的幽灵》(Ghosts of Empire),页2)。
该隐和拉麦似乎是出于自私而动武的,而其他邪恶的人则试图证明他们的暴力是正当的。他们各种方式宣称说他们施展暴力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比他们低等的,或比较没有人性。凡是和我不一样的人,我都可以正当化他们所遭受的暴力:他们不属于我的家庭、我的邻舍、我的部落、我的国家、我的种族或我的宗教。
将暴力正当化的邪恶达到极致时,可能就会诉诸于科学。我们可以从 20 世纪德国的纳粹运动中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纳粹主义的特征和历史吸引力是复杂的,但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它对科学的利用,尤其是它利用了进化论。既然进化论教导强者以牺牲弱者为代价而生存,那么似乎可以推断说强大的种族应当支配低等的种族。纳粹科学家声称他们有科学的方式可以用来区分种族,并证明雅利安人种比其他种族(特别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优越。今天我们知道纳粹的科学是假的,但在当时却有很多人信以为真,包括一些受过最良好教育的科学家;纳粹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确实很像是从进化论的合理推断出来的结果。
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指出说当时的思想环境为纳粹主义铺好了道路:“ 整合型民族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具生物学性质的反犹太主义、优生学和精英主义以不同的力量交织在一起,提供了一种令人陶醉的非理性主义的混合物,在 19 世纪末那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快速变革的欧洲社会里吸引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中的一些文化悲观主义者(Ian Kershaw,《希特勒》,134页)。” 但是,对于进化论者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真的是非理性的吗?
纳粹党的领导人将这种达尔文主义应用于政治。希特勒宣称说:“ 政治不过是一个民族为其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一道铁律:弱者倒下,强者就会获得生命(Kershaw,289页)。” 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曾说:“ 全世界我所提到过的那些低等人,将会对身为北欧核心民族的德国、身为人类文化承载者的德国发动一场歼灭战(Peter Longerich,《希姆莱》,814页)。”
纳粹分子想要夺取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出德国。他们想把斯拉夫人赶出东欧并夺取他们的土地。出于对权力的自私欲望,他们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施加了令人发指的暴力,并用科学的理由将这些人给非人化。数百万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丧生。
奴隶制的 “ 科学 ” 理由也建立在种族优越性的观念上。近几个世纪以来,奴役非洲黑人的理由是:他们在种族上比欧洲和美国白人还低等。有些人甚至声称说奴隶制是一种文明和基督教化的制度。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暴力制度,是为了廉价劳动力而推行的。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人们用科学和道德的理由试图合理化暴力和非人道的行为。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同样也是以 “ 科学 ” 的论点来合理化堕胎;这些论点宣称未出生的婴儿仅仅是类人的组织。堕胎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合法地行使其自由。然而,他们其实是将未出生的婴儿非人化,以便合理化他们抹杀胎儿生命的行为。
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恶人利用邪恶的科学来做出道德或宗教判断,并把它们当成是客观的科学结论。真正的问题不是科学,而是滥用科学。这些伪科学的借口,其可怕之处就在于残暴且自私的非人化行为。
这些将暴力给合理化的科学理由,其基础都是将部分或全部人类降格为动物。诗人以一种非凡的方式预见到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诗篇》49 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说的,目的是为了教导他们智慧和通达的事。在这里,智慧的教导是从默想死亡的普遍现实开始的。如果死亡对于愚人和智者、穷人和富人、弱者和强者都是一样的,那么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12节)。” 人怎样才能比畜生更有意义呢?答案是要认识真理:“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20节)。” 追根究底,只有真正的智慧或通达,才使人与禽兽有所分别。事实上,只有上帝能拯救祂的百姓脱离死亡,并赐给他们永生:“ 但上帝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势……(15节)。”
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小心,避免在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之人的反应中变得自以为是。当时也有一些基督徒被希特勒收为手下,也有一些基督徒会为奴隶制辩护。我们不能把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非人化。我们尤其要向那些为堕胎辩护或实行堕胎的人表明说所有在悔改和信心中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会得到宽恕。
正如大卫在《诗篇》第 5 篇中如此深刻地描述恶人一样,他也展示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追求的公义的品格:“ 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7节)。” 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眼光应当不再聚焦自己,而是只盼望上帝在耶稣里那坚定不移的救赎之爱。如此一来,我们才能不在骄傲和自私中夸耀,而是谦卑地俯伏在我们的上帝面前。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化行为和暴力的解药。
本文原发表于《桌边谈》杂志。
罗伯特·戈弗雷博士(W. Robert Godfrey)是林格尼尔福音事工的董事长与教学伙伴,也是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荣誉校长与教会历史系的荣誉教授。他也担任林格尼尔系列教学课程《教会历史综览》(A Survey of Church History)的特约讲师,并有包括《拯救宗教改革》(Saving the Reformation),《神创造的模式》(God’s Pattern for Creation),宗教改革梗概(Reformation Sketches),《一场意想不到的旅程》( An Unexpected Journey)在内的许多著作。